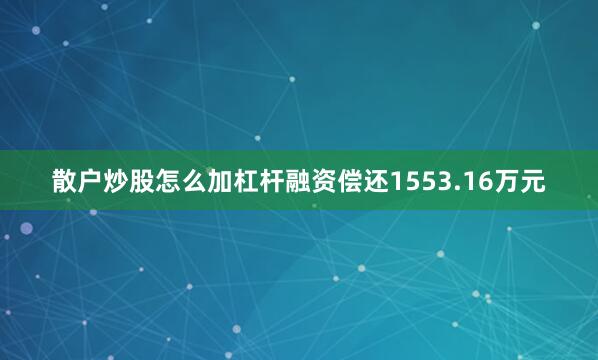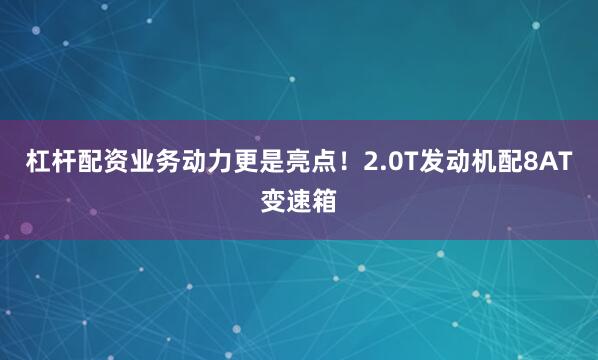图片
宋代文人吴自牧在《梦梁录》中写道:“烧香点茶,挂画插花,四般闲事,不許戾家。”这句话不仅定义了宋朝人风雅的生活方式,更描摹出一张映照宋朝人感官与精神的美学图卷。
隔火烧香、碾茶击拂、挂画澄怀、理念插花,这些被后世尊为“四艺”的雅事,在宋代并非士大夫独享的阳春白雪,也是风靡于市井巷陌的寻常生活。
图片
从汴京酒肆、食肆、商铺张挂的名画,到春日洛阳担夫鬓边斜插的牡丹;从东坡案头的一炉沉香,到临安茶肆中雪沫浮盏的点茶光影,宋朝“四艺”将两宋三百二十年光阴,凝炼成华夏文明史上最精致的美学史诗。
千年之后,宋代“四雅”仍在我们的生活里自成风雅。今人还在学着宋朝人的模样,用香、茶、画、花精致地装点寻常的生活,身体力行地向经典致敬。
宋人四雅
现代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曾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后渐衰微,终必复振。”
宋王朝“养士”政策给予宋代士大夫宽容的政治生存环境和相对富足的生活,理学与禅学的发展也一同滋养了士大夫在精神层面对文化、艺术的哲学表达和美学追求。
宋朝商品经济繁荣,市民阶层兴起,手工业高度发达,海上丝绸之路繁荣, 这些来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哲学等全方位的背景条件,为宋朝“四艺”的繁荣流行提供了最佳温床。
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不断,国外名贵香料源源不断输入,为士大夫阶层及市民阶层烧香提供丰富的香料;手工业尤其制瓷业发达,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五大官窑及各地方著名窑口生产大量瓷器,为烧香和插花提供了香炉和花瓶器具;印刷术的发明,为画谱和香谱印刷提供便利的传播条件;儒释道合流,儒家“格物致知”、道家“自然清寂”、禅宗“刹那永恒”的哲学观念共同塑造着烧香、插花、点茶的审美内核。
图片
《东京梦华录》赵盼儿点茶剧照
图片
一缕沉馥馨香,舒缓俗世烦忧。
香最早用于祭祀,《周礼》记载:“燔柴祭天”。汉代后域外香料如龙脑、沉香传入中国,但仅限贵族与宗教使用。隋炀帝奢靡焚香“一山焚沉香数车”,烧香仍属特权象征。
烧香在宋代突破祭祀与贵族壁垒,成为全民性的嗅觉审美。香事之盛,首推原料之丰。海上丝绸之路输送的龙脑、沉香、檀香,随市舶司船舶涌入泉州、明州等大港口,以至民间制香作坊兴起,“民间修合炼香日盛”。
图片
@每具万象 龙涎香
烧香,宋人“四艺”或“四雅”之首。所谓烧香,不同于宋朝以后流行的焚烧线状香品(信香),宋朝烧香主要流行用炭火炙烤,隔火熏香,以及追求香清而烟少的烧“篆香”两种熏香方式。
炭火炙烤、隔火熏香,是宋朝最住流的熏香方式。它讲究的是“烧香取味,不在取烟。香烟若烈,则香味漫然,顷刻而灭,取味则味幽,香馥可久而不散,须用隔火。”正如杨万里诗云:“诗人自炷古龙涎,但令有香不见烟”。
宋代颜博文在《香史》中云:“焚香,必于深房曲室,矮桌至炉于人膝平,火上设银叶或云母,制如盘形,以之衬香,香不及火,自然舒慢,无烟燥气”。当中已经提到隔火熏香的做法与意境的表达。
图片
@晴香阁 宋式隔火烧香
追究宋人烧香之艺,先在香炉装入精致的炭灰,以专用的香铲拨开一个小孔,放入一块烧红的木炭,再盖上一层炭灰,用香铲将炭灰堆成小山模样,再用香杼戳几个通风的小孔,这样里面的木炭才不会熄灭。然后在炭灰上放一张银片或云母,在银片或云母上放置小香烷,通过炭灰的热量炙烤香料,从而散发出香味。
宋人的“篆香”(心字香),则是将调制好的香粉放入容器内用刻有心字纹路的模具“打香篆”,最终可形成沿着心字形状燃烧的香品。
宋代词人蒋捷在他的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里写道:“银字笙调,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”这里的“心字香烧”就是宋代出现的“心字香”。
图片
@星阑美学 宋式烧篆香
宋代文人更赋予香人格化的灵性。苏轼谪居海南时,以沉香为“逆境知己”,制“雪中春信”方以寄怀;黄庭坚写《香十德》称香有十种美德,首推“感格鬼神,清净心身”。
文人雅集必有烧香。在宋画《竹涧焚香图》中,士人独坐溪畔,身旁香几上青烟袅袅——香非娱人,实为心斋坐忘的媒介。正如南宋诗人所言:“读易烧香自闭门,懒于事故苦纷纷”。一缕烟痕,隔出喧嚣尘世与澄明之境。黄庭坚被贬谪期间以香筑“喧寂斋”,借助熏香隔绝世俗烦忧。
图片
宋 李嵩《听阮图》局部 侍女侍香
图片
碾茶成粉,击拂之间,疏星皎月。
若说唐代煎茶如泼墨写意,宋人点茶则是工笔精描。宋人点茶需先将团茶炙烤碾磨,取细末调膏,再以执壶注水,持茶筅快速击拂,直至盏中涌起“疏星皎月”般的沫饽。苏轼诗句“雪末乳花浮午盏”即是宋代点茶的缩影。
图片
宋 刘松年《十八学士图》局部
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详述“七汤点茶法”,每一次注水力度与茶筅轨迹皆有法度。点茶技艺之精,逐渐从宫廷贵族走向士大夫文人阶层,并演变为风靡朝野的“斗茶”和“茶百戏”。
宋代“斗茶”,一比汤色,“纯白为上”;二较沫饓持久,称“咬盏”。黑釉茶盏因衬雪色而贵,建窑兔毫、吉州鹧鸪斑茶盏,皆是当时斗茶所用的最顶级容器。
图片
@90后茶艺师思宇
茶百戏是在点茶基础上用清水在茶汤上绘画的艺术,茶汤中图案的形成与点茶时茶汤的泡沫有密切关系。茶百戏可以使点茶形成的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,如山水云雾,状花鸟鱼虫。在宋代,人们把茶百戏与琴、棋、书并列,是士大夫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。
宋人的点茶文化后被日本僧人荣西带回日本,最终演化成日本茶道的重要一支“抹茶道”。而在“点茶”的故土中国,点茶承载着宋人更深的哲思——一盏茶汤的起灭,恰似世事无常的镜像。苏轼“且将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”之句,便是以茶筅击拂来点破人生迷障的宣言。
图片
日本茶道-抹茶道
图片
尺素千里,卧游山河,澄怀观道。
徜徉山林自然,有流水溪桥,有竹林茅舍。对于抱有政治抱负和“致君尧舜上”人生理想的中国古代文人来说,如果暂时不能归隐山林,只能把自然风景画入画卷,使之挂于堂室常伴左右,方是最好的精神寄托。
南朝云谷禅师开“卧游”之先,刘宋画家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明确提出“卧游”,此后'澄怀卧游'成为中国艺术史、美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,被后世的文人雅士所接受与推崇。
在宋代“卧游”更是被士大夫文人推到顶峰。正如米芾对挂画这件雅事的精准评论:“不下堂筵,坐穷泉壑” 。
图片
宋 《博古图》局部
宋人挂画之趣,始于雅集“曝书会”,比南朝的“卧游”进一步发展。唐以前,绘画多绘于屏风、墙壁,移动展示不便。宋代装裱技术成熟,出现“宣和裱”(天头 惊燕 地杆),立轴便于悬挂、收纳和更换,大大方便了文人在雅集时挂画评鉴。此外,宋代金石学兴起,文人酷爱搜集和收藏古画,随之画作品鉴交流日益频繁。
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《西园雅集图》,就描绘了元丰初年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16位名士在宋神宗妹夫、驸马王诜的西园聚会的情景,画中展现了文人名士吟诗、绘画、挂画、抚琴等雅集活动。
图片
宋 《博古图》局部
米芾《画史》记载,有人悬李成山水于卧榻侧,朝夕相对如栖隐岩壑。这种“不下堂筵,坐穷泉壑”的卧游哲学,使挂画成为宋朝士大夫心灵归隐的秘径。
挂画不仅彰显着宋朝士大夫隐逸山水的精神遁世哲学,它作为一种雅致的装饰物也装点着宋朝人日常生活的美学空间。
宋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》里表达挂画主张:“择画之名笔,一室止可三四轴,观玩三五日,别易名笔。 则诸轴皆见风日,决不蒸湿。 又轮次挂之,则不惹尘埃。 时易一二家,则看之不厌。......室中切不可焚沉香、降真、脑子,有油多烟之香,唯宜蓬莱、甲笺耳。 窗牖必油纸糊,户常垂帘。”
北宋汴京的饭馆、酒肆等商铺“张挂名画”成风。南宋临安的茶坊,“插四时花,挂名人画,装点店面”。 各店铺商家通过挂画装点门面,也引贩夫走卒亦驻足神游,招揽生意。至此可见,挂画之风从士大夫阶层蔓延至广大的市民阶层,成为当时社会的一时风尚。
宋代举办茶事活动时经常布置与茶会主题相契合的书画挂轴,即使在户外山林中举行茶会也时常悬挂,这就是从挂画延伸出来的”茶挂“。“ 茶挂”传到日本后,被固化成日本茶道中的基本形态,几乎在所有日本茶室中都悬挂有书画挂轴,尤其是一行书作品。
图片
日本茶室茶挂
图片
草木清姿,载道于器,理念成花。
宋人的插花,在魏晋佛堂供花和隋唐宫廷插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。唐代时,宫廷之中牡丹插瓶甚是流行,但并未广泛普及。直至宋代,从宫廷内苑贵族到士大夫阶层,再到普通市民阶层,都有插花的爱好。
图片
宋 苏汉臣《货郎图》局部
“洛阳之俗,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。”“卖花担上,买得一枝春欲放。”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的记录与李清照的词作,都印证了宋人对插花的喜爱。在宋代的全民性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汴京花市“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”。这更加印证了插花在宋代的全民性。
不同于唐代牡丹满瓶的富丽,深受理学影响的宋人创“理念花”——以梅枝斜逸示孤傲,水仙亭亭喻高洁,枯莲蓬配青瓷喻生死轮回。追求清新疏朗的风格,注重线条美,更加注重插画者在作品中表达人生哲理和品德思想,这种被士大夫赋予人格美德和哲学思考的插花美学即被称为“理念花”。
图片
宋 钱选 《提蓝图》局部
插花之艺,除了有宋人的理学渗透,还蕴含着宋人的时令审美。如宋代画家李嵩《花篮图》按季配花,春用海棠显素雅,冬用红山茶破肃杀,俨然遵循着时间秩序和意象美学。
图片
@陈香 宋式竹篮插花
插花,除了花材,还讲究花器的搭配。宋人认为,花器是插画者心性的外化。胆瓶、纸槌瓶等器形专为花艺设计。
铜觯插白梅显清刚,金丝铁线的哥窑瓶供山茶见古雅,甜腻汝窑瓶“雨过天青”的釉色衬花,更提出“酒赏为下,茗赏为上”的品鉴主张。赵希鹄《洞天清禄集》还提出“赏花需伴点茶”,因茶香不夺花韵二艺相合,方臻至境。出游携桌几“列炉焚香、置瓶插花”,成为融入宋人日常的生活方式。
图片
宋 《盥手观花图》局部 古铜觚插三色牡丹
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,在于打通感官藩篱:品茶时观画内山水,插花时闻案上清香,挂画时品盏中余甘。这种全息审美体验,将生活提炼为艺术,又将艺术沉淀为生活。
《销闲清课图》中,明代文人仍效仿宋人同室陈列四艺,但宋代真正的风骨,在于饭馆、酒肆都张挂名画的庶民美学追求。
今日我们依然在追慕那份宋人将琐碎日常点化为永恒诗意的智慧。当我们在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时,瞥见的是千年前宋朝人已经体验过的美学生活,便懂得陈寅恪所言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,原是根植于每个平凡灵魂对美的郑重相待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升阳配资-投资股票配资-股票配资资讯平台-在线配资平台网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